【导言】“我们的确是活在一个山崩海啸,天地变色的大时代。我们有足够勇气正视和迎接未来吗,还是会任由让未来淹没自己呢?萨特说得好,这是每个人都要回答,都要向自己负责的。”最近,《中国文化》杂志刊登一篇重磅文章——《论人文精神与未来世界》,作者是著名学者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陈方正先生。他在此文中指出:人类四百万年来的整个进化历程,都是由(广义的)科技变革所推动,而此历程目前已经达到一个突变点,今后人与人类社会整体的变化,将颠覆过去五千年人类文明所累积的人文观念,面对此不可测之巨变,人类必须对本身今后之命运加以深思并作出抉择。
以下是《论人文精神与未来世界》的全文,凤凰网国学频道受权转载。

陈方正,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。
现代科技进步迅速,从而令环境不断变异,熟悉的事物不断消失,以致人有如永远置身异乡,心境无时宁适。因此寻找人的本性、本质,重新发扬“人文精神”的呼声此起彼落,不绝于耳。但到底何谓“人文精神”?它为何会失落?当如何重建,又是否有可能重新发扬?那却是人人言殊,难有定论。本文所要尝试的,是撇开重建“人文精神”的崇高目标,而将之视为历史上曾经重复出现的文化现象,以将它的意义和处境看得更为清楚。这样我们自然就会想到:宋代新儒学是一个对应佛教挑战,恢复与发扬以人为本理念的运动;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中“文”的部分正是“人文主义” (humanism) ;法国哲学家萨特断言“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”;而当代新儒家唐君毅则著有《人文精神之重建》,等等。但这几个运动分别属于东西两大文明,时间前后相隔千年,彼此似乎绝不相干。那么,它们到底有无共通之处呢?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相类似的运动吗?它们与现代世界的变迁又有何关系?
这些问题的探索将引领我们面对另一个大问题,即人在未来世界将面临何种变化。在过去,这问题并不存在。在“天”抑或“神”主宰世界的时代,“人”的本质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——譬如,是具有天生仁心,或者不灭灵魂。但在科技飞跃发展的今日,这观念已经崩溃。问题不再是人的本质如何,而是人类在未来世界中将会变得如何,亦即将处于何等地位,具有何种意志、心态了。不少人可能仍然认为,未来世界既然是由人所建构,那么它也必然是根据人的意志设计,因此不可能违背人的“需要”或者“本性”。但如下面所将论及,这传统观念其实是对人,对世界的重大误解。无论如何,“人文精神”与“人性”不可分割,因此它与人在未来世界的命运亦息息相关,讨论人文精神的前景必然要牵涉到未来世界,原因即在于此。
本文共分四节,前两节回顾和分析在东西方颇有代表性的五个人文主义运动,即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、宋代新儒家、欧陆存在主义、美国的社会批判思潮,以及中国当代新儒家。后两节则分别讨论人文领域与科技的互动关系,以及人类文明演化的展望,从而为人文主义在未来世界的前景勾勒一个轮廓。这个讨论无可避免要牵涉许多似乎渺不相干的领域,因而将显得十分庞杂和头绪纷繁。至于它是否有意义,则只有留待读者教正了。
一 文艺复兴与宋代新儒学
在现代以前,人文精神重建的两个最佳例子是欧洲文艺复兴(Renaissance)和中国宋代新儒学,它们的具体发展过程与所带来的后果大不一样,但背后的精神却十分相似。我们在下面先简单描述其梗概,然后再作比较。
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
文艺复兴发源于意大利北部[1],包括“文”、“艺”两个不同部分[2],前者就是人文主义(humanism)[3]。在其初,人文主义仅指学习拉丁文法,发扬拉丁文学,有点像唐代的古文运动,随后则扩大到搜集、考证希腊罗马古代典籍,以至研究古代思想,追求古典文明的“复兴”(renaissance)。这个运动的大背景是:欧洲的希腊和罗马古典文明在4-10世纪这七百年间遭受两个沉重打击:先是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,有意识地压制异端学术;继则蛮族入侵,罗马帝国灭亡,文化火炬熄灭。
对罗马帝国来说,基督教是起源于巴勒斯坦的外来宗教,它取代原有学术文化经过三个阶段:首先,吸收希腊和罗马文明的精华;其次,通过论争贬抑俗世文学和学术[4];最后,推广修道院文化,把俗世学术从当时有识之士即教士的心中驱除净尽[5]。这整个过程经历了六个世纪(约400-1000 CE)方才大功告成。然而,到了12世纪,由于三方面的契机,希罗古典文明却又复苏之势。首先,在10-13世纪间,由于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皇帝之间的斗争,意大利北部城市乘势崛起,互相兼并,最后只剩下十几个独立成邦。它们不再依靠农业,而致力于商品生产和国际贸易,发展成富裕和多元社会,不再受教会、君主或贵族控制[6]。其次,古代希腊罗马典籍在黑暗时期失传,但被翻译成阿拉伯文,而得以保存在伊斯兰文明中。从12世纪开始,许多欧洲学者将它们翻译成拉丁文,使欧洲得以重新接触古代文明。最后,古罗马法律体系没有完全断绝,而是通过意大利北部的公证人(notary)制度延续下来。在公证人的教育中,拉丁文极受重视,那就是人文主义出现的温床[7]。
人文主义在13世纪萌芽,那时北意大利已经出现仿效古代文学体裁的拉丁文作品,它们受古罗马作家影响,主导观念从基督教转向个人意识和追求[8]。人文主义第一位大师佩特拉克(Petrarch,1304-1374)就是受其影响而崛起[9]。他出身佛罗伦萨公证人世家,虽然当了教士,却不屑处理教会事务,更不愿进修道院,一生追求柏拉图式爱情,以写作为终身志业。他崇拜古罗马雄辩家、政治家、哲学家西塞罗(Cicero),文体仿效古代的传记、史诗、爱情诗歌、凯旋颂歌、颂扬辞章、忏悔录等,由是得成大名,皇侯争相罗致,并受加冕为桂冠诗人。这样,通在罗马帝国灭亡后近千年,拉丁文学终得重放异彩。
佩特拉克对同时代学者影响极大,最重要的是佛罗伦萨的沙鲁达提(Coluccio Salutati,1331-1406)。他是著名文人和政治家,有能力和地位搜购古代书籍、文献,1397年从君士但丁堡请来名宿克拉苏罗拉斯(Manuel Chrysoloras)教授希腊文,奖励后进,掀起人文主义风气,培育了再下一代学者。其中罗西(Roberto de' Rossi,1355-1417)是希腊原典翻译家;尼可洛(Niccolò de' Niccoli,1364-1437)是藏书家;布鲁尼(Leonardo Bruni,1370 -1444)是沙鲁达提的学生和政治继承者,翻译了大量古籍,撰写了佛罗伦萨史以及西塞罗、但丁、佩特拉克等人的传记,又鼓吹佛罗伦萨公民意识和共和体制,影响日后民主政治的发展;波吉奥(Poggio Bracciolini,1380-1459)则孜孜不倦搜求和发现了大量古代手卷,包括失传已久的卢克莱修(Lucretius)长诗《自然之本质》[10]。
到十五世纪下半,人文主义开始散播到佛罗伦萨以外,这时期最重要的两位学者是那不勒斯的瓦拉和荷兰的伊拉斯谟[11]。瓦拉(Lorenzo Valla,1407-1457)推崇伊壁鸠鲁哲学,专研究拉丁文体和修辞,以证明教廷视为至宝的《君士但丁封赠书》为伪造成大名。伊拉斯谟(Desiderius Erasmus,1465-1536)凭自学成材,他多次访问英国,和《理想国》(Utopia)的作者摩尔(Thomas More,1478-1535)惺惺相惜,最后定居巴塞尔。本来人文学者绝少讨论基督教,他却起而反对经院哲学,提倡人性与宽容,又出版经过详细考证的《新约圣经》希腊文—拉丁文对照本,这在宗教改革中成为新教的重要依据[12]。到16世纪,人文主义传统还有一位殿军,即法国散文家蒙田(Michel Montaigne,1533-1592),他厌倦宗教冲突,思想倾向于怀疑论,被奉为现代哲学前驱[13]。
人文主义兴起是欧洲思想史上戏剧性的巨大转变。它毫无挑战基督教的意图,实际上却使得古代文明在罗马教会赞助甚至鼓励下复活。也就是说,人文主义者操戈入室,以最微妙,最平和与不经意的方式颠覆基督教理念,无形中瓦解了教会占据欧洲心灵殿堂的千年之功[14]。这可以说是人文精神重建的最成功例子,它显示欧洲古典文明是如何丰富、强大和坚韧,虽然经过千年沉睡,仍然能够破土而出,焕发新生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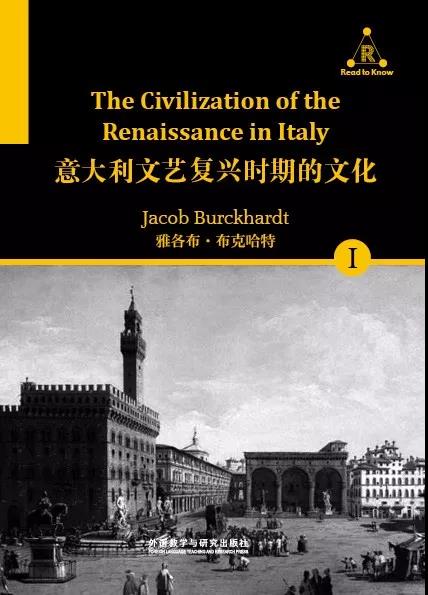
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
宋代新儒家
宋代新儒学出现的背景和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表面上有些相似,但底子里则大不相同。相似之处是,自东汉末年以来佛、道两教在中国蓬勃发展,到宋代已经有七百年历史,它们在思想、社会和政治等三方面都对儒家构成极大挑战。首先,佛、道各有一套形而上结构和玄妙理念,那是原始儒学所缺乏的,因为它向来不谈“性与天道”,而专注于人间秩序,故此“儒门澹泊,豪杰多为方外收尽”。其次,儒学以君子即社会精英为教诲对象,因此无法在民间与普世性信仰如佛道抗衡。最后,自隋唐开始,历代君主一面倒崇奉佛道,韩愈发起古文运动,却因谏迎佛骨而“夕贬潮州路八千”,那正好说明当时儒学地位之严峻。
两个运动不同之处在于,新儒学的兴起有很强的政治背景[15]。宋代自开国便处于军事弱势,而为了改变前代兵骄将悍的格局,君主又要崇文抑武。士大夫由是生出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与承担,以及与君主“共治天下”的期待与自信。而这自信则是通过儒家“内圣外王”的观念建立起来的[16]。除此之外,它的思想渊源也相当复杂,不但将儒家经典的范围扩充到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和《易经》,而且与佛、道二教也有千丝万缕关系。
整体而言,宋代新儒学的出现大致有三条脉络。首先,它的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陈抟老祖(约871-989)[17],那是一位时代跨越唐宋,通过《易经》象数和《老子》来讨论宇宙生化原理的道士,他的河图洛书之说影响了邵雍(1011-1077)和周敦颐(1017-1073)。陈抟是山林隐逸;邵雍与司马光交厚,大隐于市;周敦颐则一度出仕,他就是将易、道思想与儒学结合的关键人物,与王安石有交谊,亦曾开导二程。其次,新儒学的中心思想是“内圣外王”,即深湛、完善的内心修养是舒展政治抱负,安排合理人间秩序的必要条件,而后者又是前者的最终目标,两者浑然一体,不可分割。这个观念发微于韩愈,在王安石变法时颁行的《三经新义》中提出来,最终为二程和朱熹所接受。换而言之,新儒家是通过“道体”、“道统”和“治统”的论述,将他们修养心性那一套自省功夫作为政治改革基础的[18]。
最后,新儒学和佛教也有千丝万缕关系。韩愈排佛,宋初的柳开(948-1001)、欧阳修(1007-1072)承接其古文运动反对佛教;宋初三先生孙复(992-1057)、胡瑗(993-1059)和石介(1005-1045)虽然曾在寺庙借读,也同样从传统儒学角度辟佛。然而,此时的高僧如智圆(976-1002)和契嵩(1007-1072)禅师高瞻远瞩:他们精研韩文,一方面对韩愈和柳开等的辟佛作出反击,另一方面则承认儒学在治国方面的功能,并经常与士大夫交接谈论,由是左右舆论。其影响所及,《中庸》从《礼记》被抽出来成为朝廷特别重视的独立篇章,也很可能是出于有佛教背景的士大夫之推动[19]。因此新儒学与佛教虽然对立,亦不乏深层内在联系。
综括而言,新儒学是通过吸收《易经》和佛、道思想,来深化和扩充原始儒学内涵。它在北宋兴起,至南宋发扬光大,到明代更由于王阳明提出“致良知”之说而从士大夫扩散到民间下层。然而,它缺乏超越此生的论述与应许,所以无从蜕变为大众化宗教,扭转佛、道盛行不衰的大趋势。至于在政治上,它亦只成败参半。朱注《四书》成为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,无疑再度确立了儒学在国家体制中的独尊地位。但司马光的新政和安石的变法同以失败告终,明朝更转向君主独裁,由是书院被禁毁,以廷杖凌辱大臣屡见不鲜,“得君行道”和“共治天下”的理想完全幻灭。王阳明之从“内圣外王”转向以内省为中心的“致良知”说,缘故实在于此[20]。
两个人文主义运动的比较
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和宋代新儒家有惊人相似之处。它们都代表以“人”为中心的古代文明精神(这在中国是儒家,在西方是希腊和罗马文化)被外来宗教(在中国是从印度传来的佛教[21],在西方是从巴勒斯坦传来的基督教)渗透、掩盖甚至征服之后,由于具有古代文化意识和自觉的学者之努力,古代文明得以重新振兴,并且发展出更丰富和深刻的内涵。所以两个运动都不折不扣是“人文主义之重建”,也就是在已经被宗教主宰的世界中,重新彰显人本价值和精神。这显示,全面感染中国和西方的高等宗教虽然声势浩大,但具有深厚底蕴的古代文明仍然蛰伏于集体意识之中,时机成熟就能够破土而出,焕发新生命。它们另一个相似之处是,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学者几乎全部任职于罗马教会或受其供养,而推动新儒学的士大夫则多与禅师、佛徒、道士密切交往,思想亦交互渗透影响。这反映新旧两种文化力量虽然在理念上并不一致,但代表这两种力量的人却不一定互相排斥,积不兼容,而可以和平共处,甚至密切交往。
但从后果看来,则这两个运动的影响力却相去甚远,不啻霄壤。在社会上,新儒家未对佛道二教产生强大冲击,更谈不上颠覆它。在思想上,它从这两个宗教(当然还有传统经典如《易经》和《中庸》)吸取了宇宙生化观念和修养功夫,以充实和发展自身。在国家体制中,它重新巩固了本身的正统地位,但亦未能打破儒、释、道三者原有的势力平衡。另一方面,文艺复兴特别是人文主义则无异于掀开了潘多拉盒子,古代希罗文明尚未发挥的潜力由是得以充分释放。其最重要的三个后果是:首先,16世纪发生宗教改革和随之而来的宗教战争,罗马教会定于一尊的格局由是崩溃;其次,它间接促成了17世纪科学革命,由是完全改变人对大自然的观念。最后,以上两者转而导致18世纪启蒙运动,那带来了理性主义、世俗化思潮以及法国大革命,现代世界就是从这些翻天覆地的巨变中产生的。